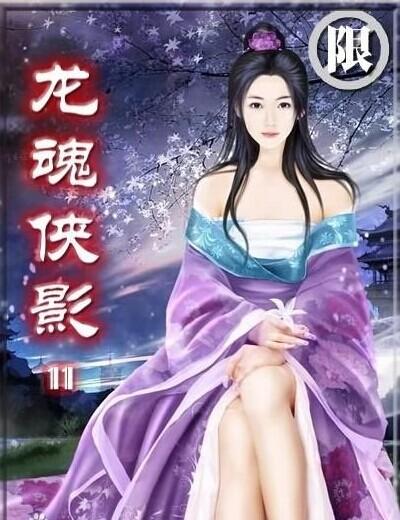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22章(第3页)
过了两天,我就离开了哥廷根。
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。
坐在车上,同来时一样,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,错综纷杂。
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,一一奔凑到我的眼前来;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,具体多了。
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,有一个特别清晰、特别具体、特别突出,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。
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,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。
1980年11月在西德开始
------------
西谛先生(1)(图)
------------
五十年代末在北大。
当时的季先生已如他敬仰的西谛先生一样,被很多学生敬仰。
1962年季先生出访埃及、叙利亚、伊拉克等国时与吴晗(右三)等合影。
频繁地出访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作家难以推辞的政治任务。
西谛先生不幸逝世,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。
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,我正在莫斯科。
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,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
我是震惊多于哀悼,惋惜胜过忆念,而且还有点儿惴惴不安。
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,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。
我百感交集。
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。
从那以后,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,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。
每一想到,都不禁悲从中来。
到了今天,震惊、惋惜之情已逝,而哀悼之意弥增。
这哀悼,像烈酒,像火焰,燃烧着我的灵魂。
倘若论资排辈的话,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。
30年代初期,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。
但是从小学起,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。
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,在清华兼课。
我曾旁听过他的课。
在课堂上,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,掌握大量的资料,讲起课来,口若悬河泻水,滔滔不绝。
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,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