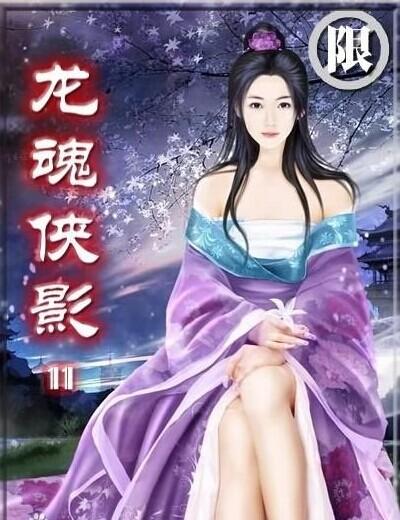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33章(第3页)
那天吃的是炸油饼,他们吃油饼就蒜。
我说:&ldo;吃油饼哪有就蒜的!&rdo;一个河南籍的炊事员说:&ldo;嘿!你试试!&rdo;果然,&ldo;另一个味儿&rdo;。
我前几年回家乡,接连吃了几天鸡鸭鱼虾,吃腻了,我跟家里人说:&ldo;给我下一碗阳春面,弄一碟葱,两头蒜来。
&rdo;家里人看我生吃葱蒜,大为惊骇。
有些东西,本来不吃,吃吃也就习惯了。
我曾经夸口,说我什么都吃,为此挨了两次捉弄。
一次在家乡,我原来不吃芫荽(香菜),以为有臭虫味。
一次,我家所开的中药铺请我去吃面,‐‐那天是药王生日,铺中管事弄了一大碗凉拌芫荽,说:&ldo;你不是什么都吃吗?&rdo;我一咬牙吃了。
从此,我就吃芫荽了。
后来北地,每吃涮羊肉,调料里总要撒上大量芫荽。
一次在昆明。
苦瓜,我原来也是不吃的,‐‐没有吃过。
我们家乡有苦瓜,叫做癞葡萄,是放在瓷盘里看着玩,不吃的。
有一位诗人请我下小馆子,他要了三个菜:凉拌苦瓜、炒苦瓜、苦瓜汤。
他说:&ldo;你不是什么都吃吗?&rdo;从此,我就吃苦瓜了。
北京人原来是不吃苦瓜的,近年也学会吃了。
不过他们用凉水连&ldo;拔&rdo;三次,基本上不苦了,那还有什么意思!
有些东西,自己尽可不吃,但不要反对旁人吃。
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,谁吃,就是岂有此理。
比如广东人吃蛇,吃龙虱;傣族人爱吃苦肠,即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粪汁,蘸肉吃。
这在广东人、傣族人,是没有什么奇怪的。
他们爱吃,你管得着吗?不过有些东西,我也以为不吃为宜,比如炒肉芽‐‐腐肉所生之蛆。
总之,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,&ldo;南甜北成东辣西酸&rdo;,都去尝尝。
对食物如此,对文化也应该这样。
切脍
《论语&iddot;乡党》:&ldo;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
&rdo;中国的切脍不知始于何时。
孔子以&ldo;食&rdo;、&ldo;脍&rdo;对举,可见当时是相当普遍的。
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提到切脍。
唐人特重切脍,杜甫诗累见。
宋代切脍之风亦盛。
《东京梦华录&iddot;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》:&ldo;多垂钓之士,必于池苑所买牌子,方许捕鱼。
游人得鱼,倍其价买之。
临水斫脍,以荐芳樽,乃一时佳味也。
&rdo;元代,关汉卿曾写过&ldo;望江楼中秋切脍&rdo;。
明代切脍,也还是有的,但《金瓶梅》中未提及,很奇怪。
《红楼梦》也没有提到。
到了近代,很多人对切脍是怎么回事,都茫然了。